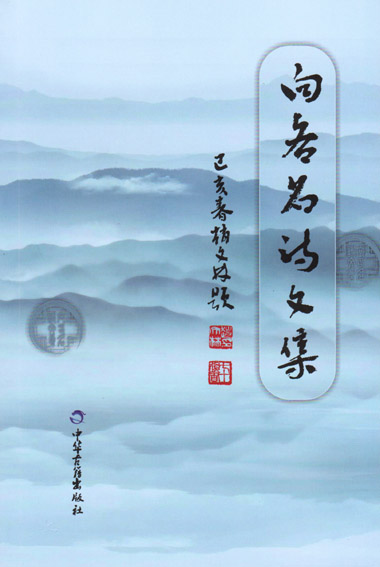联系我们
书籍详情
向各名诗文集
自 序
我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随后一直跟随大伯父生活经常遭受大伯娘的打骂,二伯的儿子就打算将我送到我外公家去,但我不想去,因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去过母亲娘家,每次都是母亲带着我去的。外公家生活比较富裕,大院的右边有戏楼,时不时会请戏班来唱戏。母亲姐弟俩,但我很少见到舅舅。记忆中的外公总是身穿长衫,头戴博士帽外婆是小脚女人,两个侍女跟前随后,不离身边。虽然外公家富有,也许受父亲影响,执拗的我也不愿去,最后负气只身离开了大伯家。
老家安江是沅江畔一座小城,湘黔公路穿城而过。离家后我在江边码头的渡轮上遇上了一位货车司机,好心的收留了我。跟着他到了贵阳,可不知何故? 刚到贵阳司机便被抓了起来,我也跟着进了牢房。几天后我被放出来,从此在贵阳街头流落,白天乞讨,晚上就睡饭馆的灶门口。记得一天夜里,天下着雨,我边走边哭,一位夜里帮人守摊位的老汉(后来知道他姓彭)听到哭声后来到我身傍问话(当时我的口音还是湖南话 ),他知道我的遭遇十分同情,还买了碗汤圆给我吃,那天我就在他守的摊位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老汉向摊主讲好话,收留了我。摊主的儿子比我大几岁,在正谊中学读初中。他对我很歧视: 常常嘲笑我是捡来的。待了大约三个月左右,摊主将我送给了一户从四川来的王姓人家。此人名为算命先生,招牌上写着“不由人”实为国民党的某党部书记,还配有手枪。解放前夕他们一家带着我返回了四川岳池县。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以为我睡着了,就跟他岳父母说,在离开贵阳前原本是打算将我卖给贵阳庆筑川剧社(后贵阳川剧团)以换得壹佰元大洋的,后来一想又算了,还是带回去种一辈子庄稼,做个长工得了。因他本身有儿女,不舍得让他们做重活。他又说,这龟儿子尖得很(当地土话),不能让他读书。我在王家受尽大人小孩们各种凌辱和打骂,说我不要脸跟着姓王,说我是野儿、杂种等等。五二年的冬天,王家就叫我脱掉裤子学耙冬水田。因为四川的耙较大,人提不动,就赶着牛一圈一圈螺纹状地由大到小(又名螺丝转顶),从此以后每到农忙季节下雨时头戴斗篷身披蓑衣犁田耙田栽秧,秋收后犁旱田种小麦胡豆,然后再犁耙冬水田,所有农活都要会做。晚上与牛为伴睡在牛圈上面,有时感冒发烧生病也没人管。王家人经常说我是“无娘儿,天照应”。冬天农闲时每天早上我便牵牛出门吃草,下午上山割草喂牛。割草时往往能在草从中捡到桐子,我就将桐子收集堆放在一起,等到桐壳腐烂后挑出桐籽,到赶场时将:桐籽换成桐油,读夜校点灯用。后来收桐籽的事情被王家知道了,他们没收了我所有的桐籽,并不准我读夜校。在王家几年里我也曾经想过离开他们家,但身无分文只好默默的忍着。记得五四年初冬,我将捡来的桐籽偷偷地剥去皮请陈永斌在赶场时帮我卖掉,最后得了五角钱,这是长这么大以来我第一次有了钱。五五年肃反运动开始,姓王的犯罪再次被逮捕(因五零年初曾被逮捕关押了两年多,五二年夏天才从监狱放出),所以肃反运动他再次被拘捕后我立即要求与他脱离关系。那时只知道自己姓向,我琢磨每个人都各有各姓,各有的名,于是我给自己取名为向各名。而且自己的真实出生年月日也并不知道,只记得四六年初夏到贵阳初秋时换下第一颗牙齿,以此来估计自己年龄。
从王家出来后,自己依然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区长刘天高听说后就与学校商量将我安排进学校当工友,做些打扫办公室卫生、搞油印、敲上下课的钟、采买东西等活路。空闲时间就到教室听老师讲课,课本中的《半夜鸡叫》启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当时我就想高玉宝虽然苦但至少还有亲人,我却什么亲人都没有,我的命比他更苦,就想着也要像他那样将自己经历写成小说。
当工友期间我买了人生中第一本书,《中国新诗选》后来还买了《李杜诗选》,开始尝试着阅读。遇到不认识的字我便请教老师,慢慢的逐步提高了识字水平。学校放假,老师都回家时,整个学校就只剩我和做饭的陈妈,再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无人教了,于是我买了本《四角号码字典》,摸索着查生字,从此开始了自学之路。当然,我父母在世时也曾教过我认过一些简单的字和简单的古诗句,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床前明月光”“二月春风似剪刀”和每天早晨读客堂中的“天地君亲师位”等,加上在贵阳居住时有邻居小朋友读书,我也跟着傍听,学了一点课文上的字,所以也算有些自学基础。
五七年学校放暑假我就擅自离校了。由岳池步行至合川再乘船到重庆。之后步行至基江乘火车到松坎,再乘汽车至遵义,因不够钱买遵义到贵阳车票,最后只能步行三天,一路辗转到了贵阳。先是找到了住在皂井巷岳池王家的三哥家,说了一番好话后他勉强同意让我在他家落户。因当时未经学校同意便擅自离开,户口、粮食关系都需要办理迁移手续,于是我写信给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贵以伦同志,麻烦他将我的户口粮食关系寄往贵阳并最终落户到皂井巷4号。之后我就在建筑工地做小工,住工棚。这一年国庆节刚过,王家大儿子从四川来到贵阳,在他三哥处说了很多诸如我如何不好的话,第二天三哥便派人来到工地,告诉我已经将我户口迁出了。一时间不知所措的我,呆呆地坐地上伤心的哭了起来。一位叫王碧珍阿姨见此情形赶紧过来问我缘由,我便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知了她,好心的她一边安慰我,一边告诉我可以把户口落在她市东村66号家里。就这样,户口问题终于解决了。从此,我便在太慈桥电厂工地靠着做小工来养活自己。
五八年五月新建的贵阳机床厂招工,我很快成为了一名机床厂的工人。同年六月厂里安排我赴沈阳机床二厂学习车工,经过半年学习后,五九年元月返回贵阳在金工二车间正式成为一名工人。那时还是大跃进时期,工厂三班倒。每逢我上白班,下班后我就到厂后的山坡上看书学习,厂里的同志给我取了个外号“书呆子”。有时候我也学着写点小诗,有的还被刊登在厂里黑板报宣传栏上。后来厂里成立工会宣传组,我成为了一名宣传员。随后小河片区的工厂联合成立文艺创作组,加入创作组后,我与矿山机器厂的很多文学爱好者结识成了朋友,慢慢开始在本地刊物上发表诗歌。六五年大搞三线建设,我被调往贵州省机械厅为新建工厂做机械设备方面的筹备工作,在闲暇的时候依然坚持诗歌创作。文化大革命时我还参加了一个叫“文艺兵”的综合性文艺组织,团里组织各种不同的文艺活动,如文学、美术、歌舞、表演等等,后因工作繁忙,又经常出差最终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一九七一年趁着到湖南长沙出差的机会,我顺道回了趟安江,想看看能否能找到自家的老家。到安江后根据自己对老家方位的记忆向当地人到处打听询问。我介绍了家里的情况:父亲三兄弟,老二先去世,留下的儿子跟随大伯父生活。之后老三(即我父亲)也去世,留下的儿子(即我自己)也跟随大伯父生活,不久后离家。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当地人一时都很难再回忆得起来。第二天我又到邻近的地方继续寻找,但还是没有结果。第三天我又回到之前的地方继续打听,这时我寻亲的事都已经在当地传开了,知道消息的人很快带着我到了二伯儿子家,终于,我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堂兄(二伯儿子)说,前两天他们已经听说了我回来的事,正在各家旅店找我,但一直没找到。当天我住在了堂兄家。亲人相见,千言万语真不知从何说起。堂兄问及了我离开安江后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告知。随后我提及了我父亲的事,堂兄说:“叔叔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从不占别人便宜,又好打抱不平。”对大伯的自私、贪财很看不惯,经常与大伯吵架。二伯去世后,二伯儿子一直寄养在大伯家,但大伯对他很不好。一有次因为此事我父亲还责问过大伯:“你让你自己的儿子读书,而让二哥的儿子帮你家做工,你配当伯伯吗?”所以父亲兄弟俩的关系一直都很紧张。我又问他:“我只记得大伯有个女儿,没听说他还有个儿子啊?”堂兄说那时你还小,大伯的儿子一直在洪江念书,四七年高中毕业后才回老家的,安江刚解放时他就在县政府当秘书。再聊到我父亲时,堂兄说,叔叔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有时去别人家,遇到人家正在吃饭,叫他一起吃,他只是说已经吃过了。其实他并没有吃,而是回到自己家里煮白菜糕杷吃。他平时也就是将青椒切成一段一段的放点盐拌着鱼吃,过着很简单的生活。我又问及父亲的死因,才知道是痢疾夺去了他的生命。
堂兄又说,解放后他提出与大伯分家,但大伯不同意,原因是解放前大伯把两个兄弟家的田地都占了,二伯儿子说如果那时分家出去,大伯家就地多人少,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家庭成分会被划为地主,如果不分家则是富农。谈到我外公,堂兄说,他们一家在刚解放时就被没收了所有家产并遣返原籍了。至于外公的原籍是哪里我也没再继续问了。晚饭后,大伯的儿子也来了,他亲切地称我“老满”(老家称呼最小兄弟的说法),先问了我离开’安江后的情况,之后又说都是他父母不好,当年对我虐待打骂才让我从小就离开老家受这么多苦,如今大伯和大伯娘也已经去世了,只能由他代表二老向我表示谦意。随后大堂兄(大伯的儿子)也介绍了一些自己的情况,正如二伯的儿子所说,安江刚一解放大堂兄就进了县政府当秘书,因为五三年土改时家庭成份被划为富农,属于专政对象,所以又调到县农业局当一般工作人员,之前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的已经当上了地委书记和专员。他感叹说自己就是吃了家庭成份不好的亏,而老满你虽然小时候吃了不少苦,但现在却比他们过得都好。我听后也只好劝着他说这可能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那次回老家终于了却了我多年的愿望,也对过去很多事情有了大概的了解。多年心愿已了,第二天我便离开安江乘车返回贵阳。每当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我想,如果没有解放,我可能将一辈子当长工,更有可能早已不在人世。是新中国将我这个孤儿从苦难中救出,之后参加工作一路从一个工人成长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而且还成了一名文学爱好若。
八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通知我该社将出版工人诗选《一朵尽开玫瑰》并向我约稿,于是我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此后我在贵州省总工会创办的《贵州工人作品选》上发表了诗与散文,并加入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其间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也曾向我发来进修通知,最终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忍痛放弃。
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盛行,我却对此一窃不通,不知如何下笔。后来文友说,你写的诗都是短小精炼,有点古诗的品味,不妨学作古体诗吧。就这样从八七年开始,我起步学习古体诗词创作。刚开始对平仄押韵相当陌生,在省诗词学会老师们的指导下才逐步掌握了基本知识,并阅读诗词学会自办的《爱晚诗刊》边读边学。后续又学习了王力先生编写的《汉语诗律学》,逐步提高创作水平,作品基本合乎了格律、平仄和对丈的要求。为了鞭策和鼓励自己还写了四首小诗聊以自嘲(见《自嘲》)。
自学习诗词三十余年来,共累积创作了一千五百余首诗、词。这些作品抒发了自己对祖国大好河山、风俗民情、时代改革的赞美之情。多以田园风光,秀丽山川及新生活新气象为多。
回看我的一生,自己从未接受过一天的正规学历教育,但靠着自己对文学诗词的热爱,再加上自认的一点小聪明学习古人写了些不敢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与真正诗词艺术家相比还只是一位初学者,比如个别作品中偶有犯孤或意境不深等毛病,敬请方家指导和教正。
后学向各名
版权所有 中华古籍出版社 2012-2028 保留所有权利
技术支持:易单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