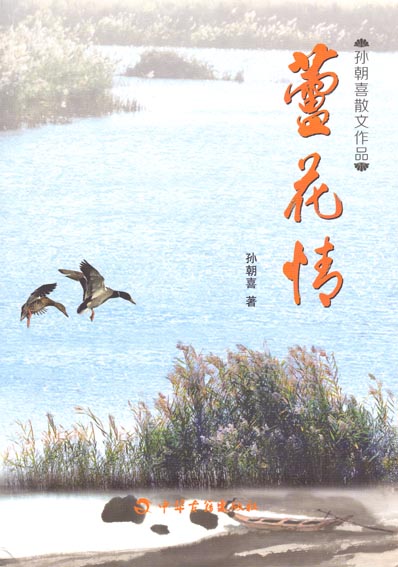联系我们
书籍详情
芦花情
作者简介:
孙朝喜,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人,生于1951年。1969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曾参于成昆铁路、襄渝铁路、京通铁路建设和唐山抗震救灾。转业地方工作后,曾任文化局副局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机关党委书记、环保局党组书记等职。退居二线后,消遣于散文创作。多篇文章发表于报刊杂志。 《军魂铸就的英雄史诗》曾荣获江苏省委组织部、省老干部局“回首激情岁月”征文一等奖。主编《群众斗争英雄谱》、策划编导纪实专题片《期盼》、编辑出版《生命的回响》。连云港市作家协会会员,灌云县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与杂文的无缝对接
——谈
王家业
捧读
作者以敏锐的视角、精巧的构思、含蓄的手法,或故事,或隐喻,或幽默,客观而深刻地表现了人的进取、浮躁、荒谬乃至丑陋,避开空泛的抒情,把杂文和散文不留痕迹地无缝对接起来,形成了极具个性特征的创作风格。作品里的文字,既清新甜美,又辛辣刺激,稍加咀嚼,就能从醇厚的美感中,品味出隽永的内涵,读来不禁让人浮想联翩,意味深长。
朝喜先生善于将生活中的人和事演绎成脍炙人口的故事,不露锋芒地倾吐和宣泄心中以至大众的爱和恨、褒和贬、企盼和心声。读者在沉湎于故事喜怒哀乐的同时,大脑洞开,有恍然大悟之感。
《捕鼠记》一文,作者从鼠患给主人翁带来的祸患,到老鼠的狡猾和惊险有趣的人鼠大战,颇费心思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把人的思绪从扑朔迷离的故事中,一步一步地引向了当前的反腐斗争上来。读者的认识从鼠患不除人们休想安宁一下子提升到贪腐不反中国梦难圆的高度上来。值得一提的是,文章末尾一句,颇令人玩味:猎鼠非但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还得请只花猫来”。“请只花猫”的弦外之音再清晰不过地告诉人们,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加大反腐斗争的力度;人民群众需要的不是反腐口号,需要的是反腐的成效。
《愚公移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作者杜撰了一个另类的《“愚公”移山》,既吸引了读者的好奇心,又对两种“愚公”迥然不同的境界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谁美谁丑,提倡什么,反对什么,读者在体味故事趣味的同时,答案也就豁然明朗了。《凝眸红灯》讲述一男子因为闯红灯被女友毅然决然地踹了;有了教训,在新女友面前,老老实实地等红灯,不料还是被新女友气急败坏地踹了。这个故事折射出了因为价值观的差异,而导致那位男子陷入“二难推理”的窘境,读来让人忍俊不禁。
隐喻,是作者常用而且十分娴熟的创作手法之一。作者把要批评的对象用“马赛克”遮蔽起来,转弯抹角、含沙射影抑或指桑骂槐地进行一番“戏说”,集趣味性、可读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犹如大厨选用上佳食材,精心烹制而成的鲜美的心灵鸡汤,让读者于冥冥之中茅塞顿开,恍然领悟其中隐含的奥妙,不禁拍案。
《盲道》中的盲人,在盲道上走得正,方向明,而一些明眼人即使走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可一不小心就走下了道。那是因为盲人“心在道上,道在心中”;所谓明眼人,面对纷繁喧嚣的世界,心猿意马,左顾右盼,甚至偷采路边野花,怎能不下道!作者把盲人和“明眼人”进行了巧妙对比,情景交融,举一反三,寓“简单”道理于故事之中,能不触发行走在道上的明眼人的认真思考和警觉?
北川灾后分房,人民群众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照顾少数官员们的平庸方案,仅凭一台摇号机,令人头疼的分房难题,“小球滚滚解决了”。作者在《拒绝平庸》一文中,用摇号机隐喻人民群众长久以来对暗箱操作的不满情绪以及对公开、公平、公正的渴望,发人深省。作者的智慧和信手拈来为创作所用的功夫可见一斑。
幽默诙谐的语言,犹如飞舞在《芦花情》里的夜萤,亮人眼目。我也常常会被作者的生花妙笔戳中笑点。在享受生动俏皮而又华彩熠熠的文字的同时,还会有一种抵挡不住的冲击心灵的感受。在没有空泛的说教而富有哲理的文字里,让人顿受启悟,一种道理,一个观点,会自动地从脑海里蹦出来,是那样的鲜活,那样的明晰,那样有说服力,那样充满正能量。
人们时刻挂在嘴上的“称谓”,本无可厚非,但作者却从称谓的骨子里捕捉到了隐藏在其中的密码。为此,作者创作了一篇拙中透秀、朴中有雅、含蓄带刺的千字短文——《打转在舌尖上的职场称谓》。为官者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以及一些人为了逢迎拍马,在称谓上费尽心思。于是,围绕称谓闹出了许多令人喷饭的笑话。看似再平常不过的称谓,作者却从中点出了官场上和社会上的一些人追名逐利、趋炎附势以至信仰危机的内在实质,也让读者从“小事”里面读出了“大文章”。
在利益至上的今天,一些人唯利是图,把雷锋形象别有用心地植入商业广告,把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和“廉价”相提并论。《三月的反思》,作者对那些一切向钱看,视公序良俗、职业道徳于不顾的无耻伎俩,既义愤填膺地予以了挞伐,又幽默风趣地进行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嘲讽。在“嬉笑怒骂”中,一泄读者的心头之愤,并旗帜鲜明地维护了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商业道德。读者也从中感受到了作者对高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坚守和不懈的倡导与伸张。
《商人·书包与孩子》,作者用“电磁动力遥控自制书包”的假想,用滑稽生动的语言,对喊了多年的减轻学生负担的口号,但时至今日学生负担却越来越重的现象,予以了调侃、反讽,在让读者莞尔的同时,更让人对学生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而不安、忧虑。
作者在《打上点滴好读书》一文中,拿自己开涮:平时很忙,无暇读书,只有在医院里挂水时,才“猪八戒抱刀火纸假充读书郎”。再看《吾佛慈悲》,揶揄一些人只知点蜡焚香,却不愿读书、不思修养。这无疑是提醒读者,长此以往,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这两篇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自嘲,或讥讽,或劝谏,看似漫不经心,谈笑风生,却让读者思绪纷飞。也从一个侧面流露出作者对当下人们的精神匮乏和民族文化危机的深深忧虑。
二零一六年八月
版权所有 中华古籍出版社 2012-2028 保留所有权利
技术支持:易单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