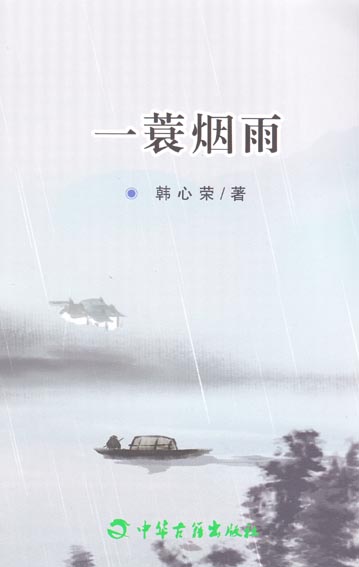联系我们
书籍详情
一蓑烟雨
作者简介
韩心荣,笔名韩枫、王菇。1946年生,安徽省溪县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历任中共宿县县委组织部秘书、副部长,宿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地辖中共宿州市委常委、宿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省辖宿州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宿州市政协委员等职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顾问、宿州诗词楹联学会会长。已正式出版诗词选《潇洒集》《抱玉斋吟稿》和散文集《连心锁》《抱玉岩》《山重水复》《柳暗花明》《秋色风流》《蔷薇花开》《海天羽痕》《北窗夜话》《香雪海》《序与跋》《自传<一蓑烟雨>》等多部,主编大型宿州古今诗词曲联专集《古汴流韵》(上中下 3部)和《宿州诗词二十家》计 4 部。其诗词和散文作品散见国内报刊、入选多部文学专集并多次获奖。
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的自传《一蓑烟雨》序
韩心荣
19 世纪末,南太平洋塔希提岛,金色的落日下,孤独而苦闷的保罗·高更站在悬崖上,面对浩森的大海和无际的苍穹,伸开双手,发出关于人对生命意义的三个终极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三个追问,惊世骇俗,回响百年,启人心智,奥妙无穷
这是一个渺小生命面对无限时空的困惑与迷惘。这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与外界事物在强烈冲撞发出的悲鸣与叹息。这是一个个体无法融入大千社会带来的无助与沮丧。
我和保罗·高更一样,也一直生活在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和我的生命有无意义以及如何才能使之有意义的巨大问号之中并苦苦寻觅着答案。
无独有偶,且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欧,德国18 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主张“生活意志说”。他声称,物体的引力与拒力,植物的向光性,动物的本能以及人的求生、求偶等欲望都是“生活意志”的表现。他认为,人是利己的动物,人的欲望在现实世界中是永远无法满足的,因而人生充满痛苦,必须断绝欲望,才能求得解脱,达到涅架。进而他说:“人生没有意义。”
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屈原在一腔忠贞报国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彷徨山野,行吟泽畔,曾对天一连发出 173 个考问。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至死也未能弄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唐代诗人陈子昂有感于浩茫宇宙下生命之短促,前途之渺茫,也曾留下千年的孤独与郁愤:“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同样,他也没有悟出“人生意义”的真谛。
19 世纪俄罗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人生的意义”却有着不同凡响的真知灼见。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
我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我对“人生意义”的基本观点虽然有人说,一个人前面的定语再多,按语法删减到最后,留下的只是“人”字,但我仍然认为:一个人仅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还要有情趣;一个人仅仅有情趣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一个人仅仅有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境界;一个人有境界是不够的,还要有胸怀。因此,做人就要做一个有才华、有情趣、有思想、有境界、有胸怀的人。这是我的人生观和终身的追求。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现实生活是严酷的。人的前途是莫测的,甚至有时是暗淡的和迷惘的。但是我十分欣赏已故诗人顾城雕刻在时光深处的那段经典诗句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
我更信奉诗人北岛那两句最有名的人生格言:“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还认为,“卑鄙”不是别人随意给你涂抹的,“高尚”也不是自己乔装打扮的,都是自己用自己的所作所为书写出来的。
我要用“真诚”抒写自己的“自传”
我要用“高尚”镌刻我的“墓志铭”。
二
也许有人会问,你韩心荣一不是达官贵人,二不是著名人物,你有什么“资格”和“必要”写“自传”?
我说,此言大谬也。
平民百姓撰写“自传”“回忆录”以及“家史”“家谱”者比比皆是,我非始作俑者。
不信?请让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范例。在北京市海淀图书城内有一家书店,门前挂着一块红底黄字的招牌,上书:“家史·家谱。传记书店”。该书店不仅出售各种家史传记之类的图书,而且专门为客户出版有关自传和记录自己家庭历史的书籍。凡有出书意愿者,提供文稿,花上几千块钱,就能拿到 50 本经编辑、审政、装帧设计、印刷的书。
老年人并不在乎有没有书号,受不受关注,能不能成为畅销书,他们只想圆自己心里的一个念想,把不会出现在历史书和新闻报道里的自己一生的经历、成就和失败、思考与感悟一一记录下来,给自己的后人留下点东西。
据涂老板统计,2009 年,他的《家史·家谱·传记书店》每个月要出10多本书;2010年,一个月出20 多本书;2011 年,每月60本到70本,平均每天出两三本。
这些普通人的传记和家史,不仅大量记载着平凡人的个体命运,而且深刻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
梁启超曾说,二十四史非史,不过是二十四家帝王将相的家谱。在传统正史的宏大叙事中,从来多见重要人物的活动,鲜见普通民众的生活。正因为如此,这些普通人撰写的完全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反而更有新鲜感。这些作为个人财富、家族财富得以编撰的书,也在客观上成了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
对于这种普通人笔下的历史,许多学者和历史学家都给予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在 1999 年发表文章指出:平民的日常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历史。正史文献中记录不足的社会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恰恰是历史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只有从这些真正的老百姓的生活状态中,才能对一个时代做出更客观准确的判断。因此他说:“只有写出来,留下了,才能进入历史”,否则就会被历史遗忘。
正如《三国演义》开篇那阔《临江仙》词所说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红?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我坚信,随着社会进步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今后会有更多的普通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历史,写自己的家族史,以抵抗历史遗忘。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能比这些听得见鸡鸣、摸得到心跳的文字是更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吗?
有人说,人生如歌。有人说,人生如梦。对我来说,皆不是之所以说它并不“如歌”,是因为它有太多的苦、太多的痛,太多的酸。之所以说它并非“如梦”,是因为它相去不远,往事如昨,清晰如画,历历如在目前
人生像一条路,一条我家乡的黑土路。常常是潮湿的,泥泞的,坑坑洼洼的,每走一步都会在路面上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
人生像一条河,一条我家乡的河。说是河,可它不宽,也不长如小溪,似小沟,既无孤帆远影,也不一泻千里,沿岸更没有旖旎的风景。它很不起眼,是一条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小河。
人生像一张纸,一张未写字的白纸。后来便有了字,并且密密麻麻地不厌其详地记录着许多东西。有欢乐,有苦痛,有慰藉,有伤怀,有高峰,有低谷,有成就,有失败,有善行,有恶为,甚至有一些至今仍不愿向别人叙说的秘密。
人生又像是一本相册。照片也是各式各样的,有黑白照,也有彩色照;有发黄的,也有崭新的;有单人照,也有双人照、集体照:有与爱人、家人、熟人、朋友的合照,也有与生人、路人、甚至“仇人”的留影。这些照片,斑驳陆离,杂乱无章,都完好地保存在我记忆的相册里。
心理学家说,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的。是的,光彩、得意的事情自然会被人们常常忆起,但伤怀和痛苦的往事更会镂骨铭心,我早有愿望,就是想把自己一生中碰到的光彩的事、得意的事和遭遇的伤怀的事、痛苦的事,通通收集起来,并摘要而成书。现在我光荣地“退休”了,实现自己这一夙愿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孩提时代发生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昨天发生的事,就像今天发生的事。这些事,像一页页撕碎了的残片,在我眼前飞舞,色彩斑斓,挥之不去,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已过“耳顺”之年的我,把这些即将飘逝的碎片收集起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既公之于世,也留给我的后人。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西游记》。当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蓦然回首,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这些磨难对我来说都是历炼和财富。
人之一生起起落落,高高低低。顺风顺水未必成就人,遭遇横逆未必就完蛋。曾有人问苏格拉底:“天地间有多高?”曰 :“三尺。又问:“人有五尺,那还不把天戳个窟窿?”苏格拉底笑答:“所以那些高于三尺的人要学会低头,才能立足于天地之间。”我以为,低头、低调、乃至夹着尾巴做人,这是一种人生姿态,也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和成就大事业的人生艺术。
生?或者死?这道选择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无法回避,我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庄子曰:天地赋予形体让我承受,赋予生命让我劳累,赋予衰老让我安逸,赋予死亡让我安息。在这里,庄子把生看作“苦役”,把死视为“乐事”。这是一种豁达的人生观、生死观。
面对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心理,庄子又说:丽姬是艾的女儿,许配给晋王时,哭得死去活来,对未来的生活充满迷惘和恐惧。当她嫁过去住进王官,每晚与晋王缠绵床第,享受美食,就对自己在室中哭泣感到好笑,早知道宫中如此舒服,还哭个什么劲呢? 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对死亡恐惧不安,是否到头来会笑自己对世界的留恋不舍,很是幼稚呢?
庄子认为,人不必执著于生,因为生若是一次远游,那么死就等同于归。视生若游,视死如归。早在 2000 年前,这位先哲就看破了“红尘”,参透了“禅机”,这确实是大气魄、大智慧。
美国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走了,人们非常惋惜地说,在这个星球上也许短时间很难再出现一个如此优秀的创新的灵魂。乔布斯的才华、激情和精力,是无尽的创新的来源,世界因他而美好。乔布斯与癌症抗争了 8 年,他开朗而豁达地面对死亡他说:“没有人愿意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终点。死亡就是生命中最好的发明,它将旧的清除,以便给新的让路。”他的话非常深刻。我们想一想,如果有人类以来人们都不死,那么地球上还有我们及我们后代的立足之地吗? 我们在自己的哭声中诞生,又在亲友的哭声中走向墓地。生命的两端都浸泡着泪水,后一次眼泪将是我们生命的终结。
天生我材必有用,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本“自传”,是我对我这一生的经历所作的一个总结。
最后,我以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的一阅词《定风波》为这篇序文作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料峭春风吹酒醒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是为序。
2012年1月6日子夜于宿州抱玉斋
版权所有 中华古籍出版社 2012-2028 保留所有权利
技术支持:易单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