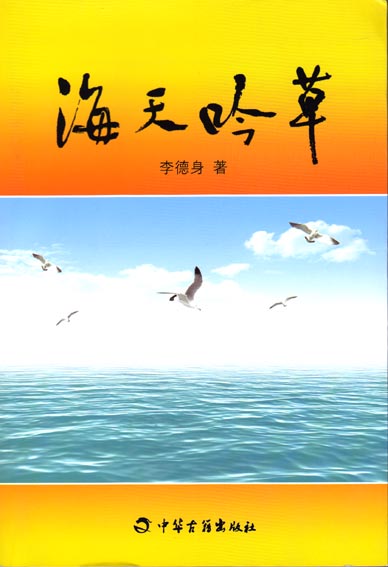联系我们
书籍详情
海天吟草
作者简介
李德身,男,汉族,1937年5月生,江苏连云港人。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毕业,任教于南充师院(今西华师大)。现为连云港师专中
跋
李德身
我是个终生与诗结缘的人。
小时候,爱唐诗,爱它琅琅上口,背几遍就记得;进中学,读新诗,喜其情辞晓畅,记不住却爱学。故在1955年刚入北京大学之际,尽管恩师均是一流学者,既有游国恩、林庚诸古典文学大师授以屈、陶、李、杜、苏、辛之诗,又有王力(字了一)这样的语言学权威授以格律诗词音韵之学,却仍醉心于《女神》《红烛》,乃至博览拜伦、海涅、普希金、惠特曼。当时班上有同窗诗友四人:孙玉石、孙绍振、张厚余和我,彼此切磋,竞相激励,并在北大学生会主办的《红楼》文学杂志上发表新诗,蔚为一时之盛。
谁知诗能动人,也能启祸。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诗友张厚余热情洋溢地写首要发扬北大民主传统,扫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三风的新诗,抄录在报纸上送给我看,我极口称赞,毫不迟疑地在诗稿下方也签上自己的姓名。结果竟招来厄运,一起被打入另册。 青春折翼,诗趣不改。只是避开涉及时事的新诗,刻意改写涵咏风物的传统诗词。1960年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大西南的南充师院,却意外幸运地叫我任教古典文学,客观 上成全了我沉心研究诗词、写作诗词的夙愿。由于接受了教训,再不上“阳谋”的圈套,因而尽管步步难行,但是带给中华民族深重灾难的“文革”并没能使我再蹈覆辙。直到1978年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我才获得彻底的解放,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记得还是在1963年深秋一个风雨交加的午后,我乘船由南充市到龙门镇去搞函授,突然听到嘉陵江号子远远地传来,一会儿就看见江边有一群纤夫吃力地拉着一艘木船正逆流冲滩。我的心似乎受到了猛烈的撞击,一路上哼着哼着,竟哼成了一首小诗:
“岂惧霜江透骨寒,风风雨雨等闲看。
冲滩号子青山应,回首烟云天地宽。”
在三年大饥荒之后,面对底层百姓顽强生活的景象,我的心灵颤动了。我用前三句写实,结尾句想象,表达了我对劳动者生命力的尊重和崇敬,寄托了自己的遭遇,胸襟和期望。由于担心文字狱的迫害,我曾将写有数百首诗作的“,隋韵录”,在“文革”大兴抄家风之际抛进了嘉陵江,但有几首纯写风物、自觉有味的诗作,包括这一首,我却特意地保存了下来。如今拉纤早已成了绝版的历史,纤夫也成绝迹的职业,但这首出于真实纪录的七绝却已成为我永恒的纪念。
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写诗是存有风险的,那么,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则给人们不仅带来物质的丰富,更带来精神的自由。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随着时代大潮的汹涌澎湃,传统诗词也由长期低迷而复苏。我适逢其会,1986年受到时任副市长的新中学长胡为德邀请,为市里创办的老年大学学员讲授诗词,使我有机会把业余写诗谈诗当成正事办。1987年又受到市委书记叶至俊派人发动,而参与创建市诗词协会工作,担任副会长兼任会刊主编,从此大弄诗词而一发不可收。由于自己发愤要将被耽误的宝贵光阴抢回来,夜以继日地拼搏,著作也便一部接一部地出版,职称也
在此期间,最令我难以忘怀的一件事,就是1 990年我们北大中文系1955级同窗毕业三十周年纪念会,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当年同室学友费振刚要我代表曾遭冤屈而落难的同学讲话,我便当着济济一堂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老同学,还有林庚、吴组缃、冯钟芸、吴小如诸位健在的恩师,一边朗诵一边解说在赴京路上再三推敲的一首七律:
“一别燕园三十年,几多往事若云烟。
频遭磨难情犹热,屡阅沧桑志愈坚。
顽铁成钢须百炼,嫩驹化骥待千鞭。
今朝无悔鬓霜点,不赋离骚学醉仙。”
我在台上讲着往昔事,台下一片唏嘘声。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和“六四风波”的惊涛骇浪,三十年后再见面的北大师生都有各自深痛的感受。也许我的诗句触动了他们心灵的思绪而引起强烈的反响。会后,费振刚传达
我虽不喜张狂,却乐观自信,乃至自嘲自慰,即使灾难加身,也极力排斥苦痛与绝望,因为我坚信“黄金总会发光”是古往今来的真理。
我的前四十年,是在不自由的状态中摸索写诗,逼近人生。我的后四十年,是在开放的情境下自由抒发,体验人生。“诗言志”,我以真善美为准则,书写心灵的履痕,从而构成我特有的诗意人生。
我曾请市书协主席杜庚先生巨擘挥写“光风霁月”四个大字裱挂墙壁,不仅作为新时代新人生明丽景象的写照,更是显露自己开阔豁达的心境。在解除思想绳索的广袤天地里,我可以象鸟儿自由地翱翔,毫不在意因言得祸了。我在大写时代新面貌,人间雅俗风,以至直斥腐败,痛骂贪官,或者怀古伤今.揭示教训,真是无所顾忌,好不痛快。
当然,既写格律诗词,必须讲究音韵,更需内涵深远,艺术高超:一定要在体现时代精神的情志美、哲理美的前提下,追求极具当代特色的语言美、意象美和境界美。我特别企慕唐人王之涣,看他在《全唐诗》中仅只留存六首诗,却字字珠玑,句句精警。诗不在多而在精,要不是厂家唠叨数量少于三四百首不成书,我真打算只选一百首,因为这已超过曹操、曹植、王粲、李煜乃至毛泽东等大家的存诗了。
私心的确曾想:如果自己也能留下几首精品给后人玩味,那该多好!
这大概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吧。当代诗运尽管随着国运复兴而复兴,但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传统诗词的黄金时代早巳一去不复返。我之所以坚持写旧体诗词,除了酷爱其语精味远而外,乃因当时特殊的时境使然。
我原本是不想出诗集的,因为自知所作无关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也不愿让它沦入供人糊窗户、包虾皮的垃圾诗那样的命运。但经不起一些知心朋友劝导,说什么即使万言不值一杯水,也可告慰亲朋诫子孙。我终于认可:既费如许心血,总该敝帚自珍,就留个念想吧。
也正因此,我极力保持其率真面貌,不事雕饰,全部依照李、杜、苏、黄的诗集按诗体分类.也不标出作年先后。读者品评其诗,仅从诗作本身即可。
好在我的北大诗友孙绍振、张厚余两位大手笔为我写了知人论世、透辟精警的序文,令我近水楼台先得月,受到许多教益和启示,我衷心地谢谢他们。我的另一位北大诗友,也曾任过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的孙玉石,自然也想请他作序,但他近来贵体欠佳,只好来日求教了。
书法家陈凤桐为我题署书名,诗友郑威则为我联系刊印,在此一并致谢!
说到底,诗是真善美的结晶,诗人是将真善美播向尘寰的雅士、歌者和好人。如果有人要问:名师、教授、特贴专家、学者和诗人诸多称呼中,你最钟情哪一个?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诗人”。
2 01 6年1月2 0日于杏坛花园海天斋
版权所有 中华古籍出版社 2012-2028 保留所有权利
技术支持:易单科技